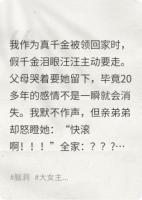湿软的泥土裹着绿叶粘连在她脚底,山路上堆积的枯枝是树木丢弃的坏死器官,她一步步踏上去,脚下的脆响跟雨声错落映衬着。
多有节奏的交响乐,她想。
三月的春风尚且还带着些凛冽的肃杀意味,刮在脸上泛着疼。她干燥乌黑的发丝被风撩起,露出一张苍白寡淡的脸。灰黑色的毛呢大衣长到脚踝,她的背影隔着雨幕与雾气望去像一道长长的鬼影。
事实上她并不清楚自己因何而来,就如同她也从来无法领略到她因何而生一样,只是冥冥中似乎有一个幻觉中的线索为她指路。那道声音对她说,“去吧,就去吧”。
“不孤,不辜。”
她暗暗思忖着,轻声念不孤山的名字。她来到这里,难道是因为她心有负债,死有余辜吗?佛说破执破妄,可是何为执、何为妄呢?佛会庇佑她吗,还是以惩戒她彰显神威呢?想到这里她不好意思的偷偷抿嘴笑了,浅淡的脸上蓦地开出清丽的百合花来。
雨渐渐停了,被阴云囚禁的太阳奋力撕开一道裂缝,光斜照着树木,星星点点的光斑铺在她上山的路上。
她收起伞,左脚突然滞住了。
寺庙门前有一颗上了年头的老槐树,树枝上倒吊着一位年轻的少女。
这位少女身上尚且穿着蓝白条纹样式的校服,身体僵直的下垂,她的双手背在身后,粗麻绳捆着她的手腕与脚踝打成死结,这像是一个忏悔的姿势。有人把她吊在三米多高的粗大枝干上,被雨打湿的头发顺从盖住她的脸,关节上勒痕的血瘀近乎黑紫色。
她站在寺庙入口,审判却早已经降临了。
她拿出手机,拨通了报警电话。
警方动作很快。在她数到树上第四百零八十片叶子的时候,一群人行装整齐地上山来了。为首的男子身形瘦长,他戴着警帽,一边转头跟身后吩咐些什么,一边挥手指示行动。
他们拉起警戒线,这颗老槐树被围困住了。她站在一旁,槐树上一颗雨珠滴在她睫毛上,凉意迫使她眨了眨眼。门前壁垒森严,门内却一片静默。他们——里面的人,知道外面发生的这一切吗?有人在里面吗?他们如此冷静是因为悟己化道,还是因为祸不及己身呢?
女法医铺好白色的尸袋,侦查员们把那个少女从树上取下来。她的身体依然微微蜷曲着,舒展不开。她的衣领与袖口处空荡荡的,在地上滩成很薄弱的一片。
“身上多处淤伤,四肢勒痕与绳子的捆缚伤一致……”
“脖颈处有一道黑红色掐痕,生前伤,或许遭遇暴力行为……”
她闭了闭眼。
“从尸僵程度和尸斑分布状态来看,死亡时间为八到十小时前,也就是凌晨十二点至两点钟……”
贴心的女警机警地察觉到她的小动作,温柔地问她是否需要休息。彼时对方正在例行问询她发现尸体的全部经过,以及她昨晚到今天的生活时间线。女警留下她的联系方式,问她是否还能继续,或是需要先离开这个事故地点先平复情绪。
她没有讲话,那位叫温郁金的大队长走上前来。他点了一根烟,笑说,“阿葵,你不太了解商小姐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