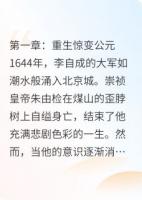我没有回家,而在家对面的酒店开了个房间。
一整天,我像个侦探,用酒店房间的望远镜监视着我们那间公寓的窗户。
窗帘紧闭,毫无动静。
楚延舟没有再联系我,大概是笃定我正在家中等他“收尾”归来。
傍晚时分,一个穿着风衣的女人出现在楼下。
她身形高挑,戴着墨镜,看不清脸。
她熟练地按了单元门的密码,走了进去。
我的心跳开始加速。
直觉告诉我,她就是那个戴着裸色指甲油,会做红烧排骨的女人。
夜色渐深,公寓的灯始终没有亮起。
直到午夜,一道熟悉的身影才出现在楼下。
是楚延舟。
他穿着我从未见过的黑色夹克,嘴里叼着烟,青白的烟雾在他脸前缭绕。
我的楚延舟,早在一年前就为我戒了烟。
他没有立刻上楼,而是靠在楼下的花坛边,烦躁地打着电话。
隔得太远,我听不清内容,但能看到他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狠戾。
他用力把手机摔在地上,又捡起来,一脚踹在垃圾桶上,发出巨大的响声。
这不是我的楚延舟。
我的楚延舟温文尔雅,连说话都很少大声。
我再也等不下去了。
我抓起房卡冲出酒店,冲进对面的单元楼,一口气跑到家门口。
掏出钥匙的手在抖。
门打开的瞬间,浓重的烟味混杂着陌生的香水味,争先恐后地涌入我的鼻腔。
那个本该是楚延舟的男人,正瘫在沙发上,看到我,眼中闪过慌乱,随即恢复镇定。
“知知?你怎么……”他掐灭了烟,站起身,想像往常一样拥抱我。
我后退一步,躲开了。
“你怎么抽上烟了?”我问。
他愣了一下,随即无所谓地笑笑:“最近压力大,偶尔抽一根。不是什么大事。”
“是吗?”我走到他面前,死死盯着他的眼睛,“那红烧排骨呢?也是你压力大,特意飞回来做给自己吃的?”